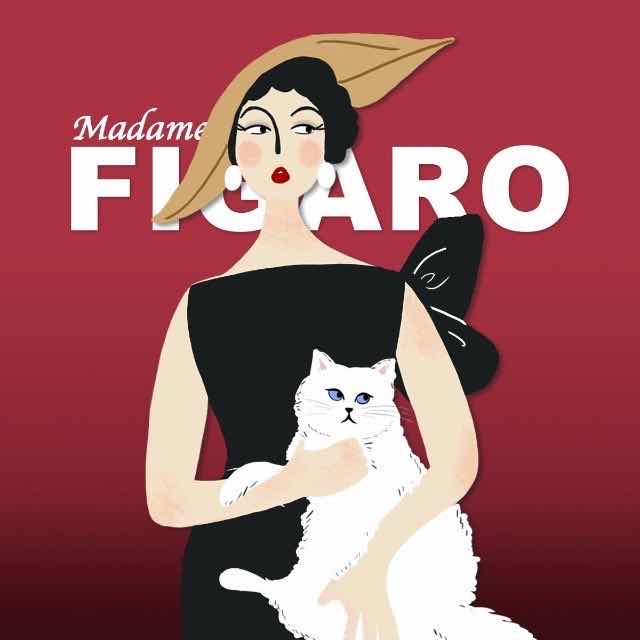男頻的爽文里,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偶然獲得機緣,一路憑借寶物、貴人逆襲,便是故事的爽點所在。
現實世界里,一個山東女人卻和兩個女兒蝸居在 4 平米的空間里,靠一雙手、一個木板車,完成了小說都不敢寫的超強爽文大女主逆襲,被香港人稱為 " 皇后 "。
憑著一碗水餃,跋山涉水的食客在她的木板車前排起 2000 米長隊;挑剔的香港人以她為原型拍攝電視長劇,將她視為 " 獅子山下 " 精神注腳;日企也甘愿為她讓步。
故事中場,她堅決拒絕了外企邀約和出海的機遇:" 吃餃子的人在中國,我不走!"
1995 年,中國香港用一部 25 集長劇來歌頌她,歌頌拼搏向上的香港精神。
30 年過去,我們再一次借由馬麗認識她——臧健和,她的故事讓馬麗在熒幕上哭,在電影宣發的時候哭,采訪談到 " 媽媽 " 了也哭。
30 年過去,還沒有出現下一個企業家能做到像她那樣傳奇。
但神奇的是,她普通到像每一個人的媽媽,她沒有天生的謀略,有的只是掌握自己人生的堅決。
■拋棄負心丈夫
臧健和第一次在生意場上談判,就引得在場所有日本商人哄堂大笑。
在她的水餃攤上,一盒餃子零售價是 11 元,她卻用 12 塊半的批發價賣給其他老板。批發價高于零售價,這顛覆了以往的商業規矩。
但她成為了第一個或許也是最后一個成功用高批發價賣出商品的女企業家。
她的一生被許多人稱之為傳奇,但又顯得格外 " 普通 ",她出身農村,沒上過大學,更沒有高人當靠山。
1945 年,臧健和出生在山東省日照市一個清貧的家庭里,父親在妹妹出生沒多久后,就以 " 外出打工 " 的名義,永遠地離開了家。
14 年后,家鄉大旱,食不果腹的母親只能帶上兩個女兒,沿街乞討,一路流浪到青島,才艱難找到容身之所。
她想要讀書,但意識到 " 如果繼續讀下去,媽媽可能就沒命了 " 后,當即選擇輟學,當小護士。
臧健和拒絕過許多人說親,直到工作穩定,媽媽生活安定,妹妹也有了工作,才和同醫院的一個泰籍華裔醫生墜入愛河,結婚生子。
日子很順利地過著,兩個女兒接連出生,處在幸福中的臧健和從沒想過,她會經歷和母親相同的不幸。
臧健和一家
1974 年,一封家書將丈夫召喚回泰國,臧健和一時無法拿到批準,必須要帶著孩子等上三年才能到泰國團聚。
三年后,丈夫依舊杳無音訊,與當年默默守望的母親不同,臧健和雖然沒出過國,更不會任何外語,但拿到批準后毅然決然地帶著兩個女兒踏上異國他鄉尋夫。
再次見到丈夫時,她也見到了他的另一個妻子,一個能生兒子的妻子。
重男輕女的婆婆并不歡迎她的到來。但泰國是一夫多妻制國家,丈夫似乎還念著一些 " 舊情 ",允許她留下。
" 在這樣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就算留下,女兒能得到什么好的教育?"
她決定離開,像母親一樣,把兩個女兒帶大。
上世紀 70 年代,婦女身處在一個緊張的時代里," 離婚 " 不是彰顯自由的代名詞,女性的人生會因 " 離婚 " 被妖魔化。
在家鄉那存不住秘密的農村里,家中或許會因她的逃離,面臨無妄之災。
還能去哪呢?從泰國中轉的飛機載著母女三人降落在香港。
1977 年的香港經濟正迅速騰飛,和韓國、臺灣、新加坡并稱 " 亞洲四小龍 ",國際貿易港口維多利亞港高樓林立,碼頭上人頭攢動,一種朝氣蓬勃的生命力,在空氣中彌漫。
七十年代的維多利亞港
當時在香港,來自內地的 " 偷渡者 " 處于井噴狀態,在內地只能一天賺 7 角錢的農民,在香港賣體力工資能翻近 100 倍。
有地方流傳的民謠唱道:" 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對面 8 分錢 " ( 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 ) 。在那里,一人賺錢養活全家人是一種看似人人都能過上的生活。
兜里只剩 500 塊的臧健和,決定留下來。
沒有學歷、不會當地語言、帶著兩個女兒單親媽媽,飽受房東歧視。
她好不容易在香港銅鑼灣羅素街,找到了一個的 4 平米合租房,房東租房有一個前提條件:臧健和的兩個女兒不能出現在客廳里。
屋里沒有窗戶,看不見白天黑夜。母女三人蜷縮于此,看不見前路。
臧健和在香港租的第一個房子
而且即便這樣逼仄的空間,房租也要兩百元。臧健和積蓄減半,需要馬不停蹄地找工作。
語言不通,她就從不用說話的 " 啞巴 " 體力者做起。早上六點多給老人打針,再去酒樓洗毛巾、洗碗、洗廁所,夜里輾轉電車廠洗公交巴士,直到夜半三更,往復循環。
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無數外鄉人夢想著通過賣力氣賺錢致富,衣錦還鄉。
臧健和也一樣。她不覺得苦,也從不向家里訴苦,她每月寄給母親 300 元,越過越心安,似乎已經看到女兒好好讀書、母親頤養天年的那一天。
可她很快后悔了,懷疑跟著丈夫才是明智之舉。
■后悔,但不求饒
" 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臧健和提起那段暗無天日的日子都會眉頭緊皺。
她在酒樓工作時摔斷了腰,工作全丟了,還被醫生告知有嚴重的糖尿病……
從未懷疑過自己決定的女人,開始動搖,她怕女兒們會成為孤兒。
" 或許當年就應該把女兒留在丈夫身邊呢?這樣她們還能有親人在身邊。"
可短暫的自我懷疑后,她依舊遵循內心的聲音,堅定地選擇,勇敢地說不,對抗不合理的一切。
酒樓老板拒不賠償,她將老板告上法院,獲得 3 萬元的賠償款和 4500 元的工資,但她只拿了工資的部分," 我真的拿了他三萬元,可能一輩子要告訴別人這個女人騙了他三萬元 "。
香港社會福利可以給她公援金補助,每月有幾千塊可拿,遠超她打工賺的錢,但她也看到不少青年靠此度日,整天無所事事,人硬生生活成了廢人。
有人勸她改嫁,找個男人依靠總比現在強,還有人勸她趁著還算年輕,去做幾年陪酒女,來錢快也不用再拋頭露面……
面前明明有那么多條路可走,但她怕 " 一人走錯,三人走歪 ",將命運拱手讓人,是比窮和苦更災難的。
絕處總有一條逢生的路,在酒樓一起共事過的同事提了一嘴:" 臧姑娘,你做水餃那么好吃,干脆去賣水餃吧。"
臧健和沒把這句話當作不痛不癢的安慰,她即刻行動,連夜做了一個簡易的木制小推車,在受傷后第 13 天出攤。
從出租房到灣仔碼頭,平時只要 15 分鐘的路程,在出攤的第一天,臧健和覺得這段路走得無比漫長。
從護士,到苦力再到無證經營的小販,臧健和回想起走來的人生路,她打心眼里難過怎么混到了如今這般田地?
" 為母則剛 " 的敘事不會天經地義般地降臨在每個母親身上,她們在面對從未有過的屈辱時,會忘卻所有附加的身份,本能地為自己的人生發出悲鳴。
碼頭上人來人往,小販和上下船趕工的工人擠滿了碼頭,但在第三根灰色柱子下,竟有一片空白之地,臧健和美滋滋選擇在那里支攤,后來她才發覺,那里是最容易被城管抓到的地方。
臧健和在擺攤的柱子下
母女三人配合默契,大女兒幫忙包餃子,小女兒放哨,一天小女兒被旁邊商販帶來的小狗吸引了目光,直到整個碼頭開始騷亂,女兒才回過神來,看見警察按著母親的攤位,她捏著警察的衣角爆哭:" 叔叔,不要拉走我媽媽,不是媽媽的錯,是我的錯,是我沒有看牢你…… " 母女三人在木板車前哭成一團。
警察抬手了,說:" 臧姑娘,你做生意吧。"
她開始賣出第一碗、第二碗……生意好了起來,可光臨的大多是碼頭上趕工的外地人,北方水餃還是不夠吸引當地人。
她注意到,有一位極其喜愛水餃的香港本地食客,每天都來光顧攤位,但都把餃子皮給剩下。
追問其原因," 皮厚得像棉被 "。聽到這句話的臧健和吃了一驚,她的水餃已經比內地水餃的皮薄了一倍,卻還遠遠不夠,皮薄如紙的云吞更受香港人的喜愛。
臧健和不想只做外地人的生意,她當即研究了三天三夜,一種在香港聞所未聞的水餃——既能皮薄透著餡,又融合著北方粗獷氣息的大水餃,出現在灣仔碼頭。
《東方日報》的記者連吃三碗后,把臧姑娘寫進報紙。
次日,許多人慕名從各處甚至澳門趕來,排起千米長隊,灣仔碼頭走出個 " 水餃皇后 ",每天生意紅紅火火。
臧姑娘沒有天降貴人的神奇故事,憑借著自己的摸索,母女三人的困境似乎擺脫了。
但臧健和明白,爆火并不能代表什么。她依舊是無照小販,每日得提心吊膽地生活。
可很快,她又堅定拒絕了到手的牌照。
■ " 最不會做生意 " 的女企業家
1982 年,臧健和在灣仔碼頭做小販的第 3 年,有人免費上門送廠房和牌照。
從幼時開始流浪的臧健和,是最會說 " 不 " 的女人。這一次,她的選擇依舊是 " 不 "。
那時,做珠寶生意的表姐,偶然帶著臧健和的水餃去參加日本老板舉辦的聚會。
日本老板有個口味極為挑剔的女兒,卻在宴會上連吃了二十七八個水餃,這一幕簡直不可思議,他立刻拜托表姐,提出想和這位奇才合作。
大老板知道臧健和只是個無照小販,他主動提出給她廠房和牌照,還要幫她把水餃放入超級市場售賣。
對方給出的條件太好了,臧健和不明白:" 那我能提供什么呢?"
老板大手一揮,她什么都不需要帶,就帶著技術來就行。
" 這句話像是給我開了一條縫 " 從未經過商的臧健和沒有當即答應,出了辦公室的門,表姐急不可耐地問:" 為什么別人擠破頭都想拿到的名額,你卻要考慮一下?"
她怕技術被別人學走了,那時品牌都成了別人的,萬一被一腳踢開中斷合作,恐怕自己都無法再販賣屬于她的水餃。
她沒什么談判的籌碼,但堅決拒絕了橄欖枝。
日本老板讓步,說可以保留 " 灣仔碼頭 " 的品牌,但要去掉包裝上的地址和電話。
臧健和再次拒絕:" 灣仔碼頭有今天全靠顧客們的意見和提醒。"
日本老板又退了一步,包裝上保留臧健和的人像和電話號碼,讓臧健和保留秘方和品牌,轉而成為超商水餃專柜的供貨商。
談判進行到第三次時,臧健和再次讓日本老板目瞪口呆,連連發問:" 臧姑娘啊臧姑娘,你到底會不會做生意?"
" 敲定價格 " 是這場合作能不能達成最后的關鍵,臧健和想了好大一陣子,說出了 12 塊半的價格。久經沙場的商業大佬們哄堂大笑,零售價 11 塊一盒的餃子,批發價居然還抬高了 1 塊半,臧健和真是個不會做生意的糊涂企業家。
她沒有被這些笑聲搞得手足無措自我懷疑,她邀請老板們去小攤看一看。
每到下午 4 點半,小攤前已經里三層外三層圍滿了食客,臧健和的手飛快,平均 2 秒包一個餃子的速度也趕不上排隊的需求,客人們開始自發當起了包裝工。
他們守在案板邊上,臧健和包一個他們就往盒子里扔一個,數夠 40 個,就拿橡皮筋扎好,把準備好的 11 塊錢扔到錢盒里,不用再找零。
需要客人打包,卻能實現零差評,水餃還是供不應求,提高一塊半的價格還讓臧健和懷疑是否定價低了,她對水餃付出的心血,遠超一塊半的價值。
日本老板對臧健和三次的拒絕心服口服,雙方達成合作。
臧健和在香港街巷租下了一間門臉房作為加工間,終于拿到了營業牌照,水餃每天直接運到香港超級市場的水餃攤位。灣仔碼頭水餃開張的第一個月銷售額就高達 100 萬港元,不到 4 年的時間,所有香港的超級市場,都成了灣仔碼頭的分銷點。
曾有外國企業邀請臧健和出海,直爽的臧健和直接拒絕:" 吃餃子的人在中國,我不走!"
直到 1997 年香港回歸時,灣仔碼頭與美國通用磨坊正式合資,臧健和則留作顧問。通用磨坊注資 6000 萬美元在中國內地設廠,灣仔碼頭開始出現在廣州、上海、北京等地。
那一年,她參觀了美國工廠,眼前成熟完善的銷售網絡和先進的冷鏈技術讓臧健和意識到,必須擁抱科技才能讓中國水餃走向世界。
女兒勸她投資到香港,一年回本,內地市場雖大,但回本周期太長。
臧健和初心未變:" 無論回本時間長短,一定要到內地投資,到家鄉投資,要為家鄉做事。當時選擇合作伙伴的必要條件之一,也是一定要到中國內地投資。"
至始至終,臧健和或許都不太會做生意,比起建立起商業帝國,她的心里眼里只有水餃。
10 年后,年過六旬的她開始籌劃中國水餃在法國的營銷計劃。
那時,她有了一個小孫女。這個家似乎冥冥之中就是個 " 女兒之家 ",從臧健和到女兒再到孫女," 水餃皇后 " 的皇冠在每一個女性手里傳遞。
臧健和絕不是最特別的一個,在那個時代下,女性正爆發著一種超越觀念和世俗的力量,全國的女人正在掙扎著站起來。
■母輩打工日記
臧健和出名后,成了那個時代的女性偶像。
上世紀 90 年代,正是臧健和事業高速發展的階段,但國內產業結構發生變化,下崗女工成了時代的眼淚。
當時的臧健和在上海和廣州都有很大規模的廠房和生產線,她的水餃業務已經覆蓋了內地 70% 以上的地區。
臧健和在上海講述她的故事,一下臺,下崗女工們就把她團團圍住。
46 歲的陳國貞,1997 年從立新五金廠下崗,她能吃苦也愿意吃苦,可到哪里都做不長。去做清潔工,不到一天就被辭退了,代替她的是個年輕的外來妹,拿著比她少得多的工資;在南京路紅心點心店洗碗,4 個月后,新來的應屆生又接替了她……丈夫殘疾,兒子在上高中,她總覺得有力氣沒地方使,想到要推車上街做生意,她和臧姑娘第一天賣水餃時一樣,面子上總過不去。
還有 47 歲的張林洪,1993 年從中華第一棉紡針織廠下崗,上街賣過盒飯但苦于沒有牌照,當過洗衣服推銷員、暑假管托班的老師、參加過剪裁培訓班和電腦培訓班……她身上有著臧姑娘的魄力,多次想帶著幾位下崗姐妹開店,但害怕失敗對不起姐妹的沉重負擔讓計劃一直延期。
她們是千千萬萬個臧姑娘,出身農村、沒錢讀書、也沒什么技能的,可只要尋著機會,就會立刻撲過去。
她們找到了自己的 " 灣仔碼頭 ",下一個機遇之地——廣東。
那時,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吸引來了第一代南下的 " 打工妹 "。
胡小燕出生于 1974 年四川廣安農村,16 歲初中畢業后就在家務農,期間做過兩年的幼兒園老師。
她想外出打工,父母阻攔,后又結了婚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她還是想走,1998 年,她跟著妹妹和妹夫趕路三天三夜抵達佛山。
" 瘋狂打工 " 是那個時代每個人身上的特點,她先做流水線工人,每天工作 12 個小時,得來的幾百元工資,比在老家種地一年的收入都要多。
2002 年,做流水線女工的第四年,公司擴建選拔人才,她抓住機會從工人變成了車間管理,一人負責招工、培訓、考核、生產等環節。
" 我常說我是時代的幸運兒 ",2008 年,胡小燕來廣東打工的第 10 年,被選為廣東省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也是我國首個從農民工隊伍中選舉產生的全國人大代表。
胡小燕(中)和其他農民工代表
許多打工妹的人生開始開出形態各異的花,有的人成了工會的女律師,有的人擁有的自己的辦公室,有人買了轎車、第一個房子……
當然還有人幾年后返鄉成家,但永遠感謝這段出來看世界的年歲。
一位六十多歲的奶奶在小紅書上寫道:" 老想說說我自己……六十歲的我,第一代打工妹中的一個,終于能在故事里分享歲月給我的一切!"
她的家在嵩縣外方山深處,汝河邊的高坡上,她排行老二,共有姐妹三人,從小就食不果腹,發育慢,別人嫌她笨都不跟她玩,家里窮得揭不開鍋了,父親還是收養了一個哥哥。
挨到上初中,她有了最親最好的閨蜜,她們會說一些悄悄話,暢想通過學習走出大山,出去闖蕩。后來,哥哥讀了高中,就再也沒錢供家里的女孩讀書,她就放棄學業,早早流落到社會上。
后來她在大理石廠碰見了丈夫,一個月 18 塊幾毛錢,多勞多得,生活水平比起在家時算很不錯了。
她會寫兩人在秋高氣爽的湖邊喝多了唱歌,走過長長的柳樹林,在沒人的地方相擁相吻。后來抵不過廠子倒閉,兩人在家鄉做起了水果生意,生意也算紅火。
不一定要闖出什么名堂來,才算不虛此行,重要的是她們曾體會過自己把握人生的自由。
近幾年的熱詞 " 原生家庭的苦難 " 幾乎落在上個世紀每一個打工妹的頭上,但她們好似從來沒放在心上,相比看到她們內心的果敢,有人將她們的經歷完全歸結于 " 時代的幸運兒 ",只是那個年代給了她們更多的可能性。
可從冒出想法到真正去實踐的人,又有多少呢?
" 一個女人去闖蕩該怎么辦?"
" 會不會過得不如嫁人?"
" 女人真的能賺大錢嗎?"
……
這些懷疑的聲音,依舊在如今 2025 年的上空盤旋。
無論放在哪種時代下,真正敢于探索未知,沒有退路可言的內核,才能讓自己真正站起來。
面對著一雙雙炙熱的雙眼,臧健和曾對下崗女工們說過這樣一句話:" 咱們女人就得自己救自己,自己倒下,別人是扶不起來的。"
如果一片貧瘠的土地無法滋養自己,不要猶豫,找到下一片沃土,總能結出自己的果。
監制 / 費加羅夫人
編輯 / 毛毛
微博 / @費加羅夫人
部分素材來源 / 網絡
戳戳" 閱讀原文 "來微博找夫人玩呀